牽著蝸牛去散步,我給孤獨癥孩子當27年老師
圖片:來自星星雨
作者:吳良生,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專業委員會委員,主任教師,教研部主任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你小子到底想做什么樣的工作?”
“我喜歡有挑戰的工作。”
“我知道一份很有挑戰的工作,教孤獨癥的孩子。你想不想干啊?”
“什么是孤獨癥?教什么?”
我的親戚沉思了一會兒,想了想,然后不是那么確定地說道:“孤獨癥,應該就是不愛說話,不喜歡跟別人一起玩的孩子吧!至于教什么?我也不知道要教什么。那樣的孩子動不動就發脾氣……總之,很不好帶。”
工作之地是遠離家 2000 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對還沒有走出過廣東省河源市的我而言,既熟悉而又陌生。然而,在那個時代里,在人們紛紛選擇南下到廣東,而我卻“背道而馳”,明智嗎?這在心理上很難選擇。
但行與不行我都得試試!
最終,我下定了決心 — 北上北京,到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以下簡稱:星星雨)工作。
牽著一只蝸牛去散步
1996 年春節過后,我在火車的硬座上顛簸了 48 個小時,終于到達了北京。
來到“星星雨”后,我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在“星星雨”學習,晚飯后就練習將白天所學的方法和技巧去教我的學生 — 文文,每天晚飯后給文文上 2-3 個小時的課。周六、周日也堅持每天給文文上 5-6 小時的課。
那時,文文 10 歲,長著一頭濃密的黑發,濃濃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時常顯得空洞和迷茫,只有看到他最喜歡的可樂和薯片的時候,才會變得明亮而熾熱。如果他如愿地得到了可樂和薯片,他就會露出一口整齊而潔白的牙齒,恬靜而幸福地微笑。
正是這樣的文文,每每看到了商店里的可樂與薯片,他就會掙脫大人的手沖過去拿。拿到之后,左胳膊抱著可樂,右胳膊抱著薯片,誰都無法搶走。
如果他沒有拿到可樂和薯片,他就會在商店大哭、躺到地上打滾、咬自己雙手的小魚際肌、用雙手的手背輪流擊打自己的下巴。因此,他雙手的小魚際肌掌面和掌背位置都結出一層厚厚的繭子,他的下巴比別人的下巴要更尖更長。
文文雖然已經 10 歲了,但他從小到現在一直都不會說話。我每天按照文文班主任制定的個別化教學計劃給他上課,發現他每次最多能坐下來上課 5 分鐘,除了能模仿一些簡單的動作,其它的課都不懂。
我模仿著他的班主任教他的方式,他要么不配合我,要么好不容易配合了卻怎么教都教不會。
忙碌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眨眼功夫,我到“星星雨”就一個半月。在這一個半月的時間里,我發現無論我怎么努力、怎么用心地去教文文,他該不說話還是不說話;無論我像耍馬猴那樣在他面前上躥下跳,他該不理我還是不理我;無論我多么熱情地帶著他做游戲,他還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做游戲。
我開始懷疑,我的努力有什么意義?我的付出又有什么價值?
在北京,只要一刮北風,我的手指關節處就會裂開口子流血,吃著和南方完全不同口味的飯菜,喝著靜置一段時間杯底就會出現一層像豆腐渣一樣的沉淀物的開水,一個月掙著少得可憐的 400 塊錢工資,我還有必要堅持下去嗎?這時,我中師的同學正好邀請我回深圳與他一起合辦微機培訓和財會培訓機構,我真的萌生了回廣東掙錢的想法。
我心理上的波動讓大家都看出來了。
田惠平老師知道了我的狀況之后,給我安排了系統而專業的培訓,培訓的主題從正確認識孤獨癥到輔導者情緒的控制,以及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ABA)的理論知識和實操技能。
▲ 1996 年吳良生在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接受“星星雨”創辦人田惠平老師的理論培訓,前排站立者為:田惠平,后排右2為:吳良生。
通過學習我才了解了什么是孤獨癥。1943 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兒童精神病醫生 Leo Kanner 報告了 11 名具有相同特點的兒童,他把這些癥狀稱之為孤獨癥(Autism)。孤獨癥是一種嚴重的終身性發育障礙,是廣泛性發育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PDD)的一種亞類型,其癥狀最晚在三歲之前即有表現。
癥狀表現為:1.人際關系及交往的本質性障礙;2.語言性及非語言性溝通障礙;3.興趣以及行為呈明顯的局限性與刻板性。孤獨癥的發生率為萬分之四,男孩與女孩的比例為 5:1(據1996年報告的數據)。
至此,我才真正正確地認識了什么是孤獨癥。
孤獨癥是一種伴隨終生的發育障礙,不是抱著一腔熱血想把他們教成正常人就能教好的。不是說他們不愛說話、不理人、不喜歡跟別人一起玩,我主動跟他們說話、多陪他們玩就能把他們變成正常人。
雖然孤獨癥兒童具有相同的障礙特征,但是他們的特點和能力水平又是千差萬別的,作為特教老師的我,要學會因人而異地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個別化的教育。
隨著學習的深入,我也漸漸地靜下心來給學生上課,每次上課都能根據學生的特點和能力水平以及他當時的配合狀況設置目標。
文文經過三個月的培訓之后,他看見可樂和薯片不會沖過去搶了,我還可以用兩根長條狀的積木替代了他時時刻刻緊抱著的可樂和桶裝薯片,不用每次出門都抱著可樂和薯片了。我每次給他上課,他最少能坐在座位上配合 30 分鐘。他能模仿比較復雜的粗大動作和精細動作,能模仿口型和吹氣。理解能力和其它能力都得到了較大的提升。
1996 年 8 月的一個中午,午休時我買了一聽可樂。
“啪”“呲”……
當我打開聽裝可樂準備喝的時候,文文小姨帶他去上廁所,正好經過教師辦公室門口,聽到我打開可樂的聲音后,他沖進了教師辦公室,眼巴巴地看著我剛剛打開的可樂。我拿來一個杯子,往杯子里倒了一小口可樂,把杯子舉到他面前,讓他能看見里面的可樂,同時讓他跟我說“要”。第一次,他很努力地做出了說“要”的口型,但是沒有聲音,我把杯子交到他的右手,他端起杯子一仰脖把可樂倒進嘴里喝掉了。喝完后,他把杯子伸到我面前,意思是讓我再給他倒可樂。
我把他手里的杯子拿了過來,又往杯子里倒了一小口可樂,把杯子舉到他面前,讓他跟我說“要”。
這一次,他用有點沙啞的聲音說出了“要”。
聽到 10 歲多了從來沒有能夠仿說一個音節的文文說出了“要”,我把杯子放到了旁邊的桌子上,站起來把雙手放在文文的腋下,把體重 80 多斤的他舉起來拋向空中,一連給他舉了 5 個“舉高高”。他小姨在旁邊聽到文文終于說話了,激動得流下了兩行熱淚。
就在那個中午,我用一聽可樂,教會了文文說:“要”“我要”“我要喝”“我要喝可樂”“媽媽”“阿姨”。他也讓我體會到了從事孤獨癥教育 5 個多月來最大的成就感,讓我理解了教育孤獨癥的學生就像牽著一只蝸牛散步一樣。
▲ Photo by Olivier Piau on Unsplash
初次被叫“吳爸爸”
我接受了“星星雨”系統而專業的培訓之后,經過嚴格的理論知識和實操技能考核,成績合格。1998 年,我終于成為了家長培訓班的班主任,可以獨立帶班了,可以根據測評結果給學生制定個別化教學計劃,可以系統而專業地給學生開展個別化教學,也可以給家長做 ABA 專業的實操技能培訓了。
▲ 中國內地孤獨癥教育工作的開展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晚了 50 年,“星星雨”的發展和我個人的成長都得到了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專業學者和專家的支持,此圖為美國的特教專家到“星星雨”提供專業支持時的合影,前排左 2 為吳良生。
1999 年第四期家長培訓班,我負責孩子能力最好的那個班級的家長培訓,班上有 10 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孤獨癥兒童和他們的家長。班上有一名叫小付的 9 歲小伙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他只按照自己的喜惡來做任何事情,社會中人們約定俗成的對錯在他身上根本沒有用。對于他而言,他喜歡的和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對的,他不喜歡的、他不想做的、人們不能滿足他的都是錯的。
開學后第二天放學時,我們班就已經精彩紛呈了,班上的九位同學都被小付打了,其中有三位同學的臉被小付給撓破了。小付想得到媽媽的關注、或者情緒不好了,他就打離他最近的小朋友。他跟同學要玩具或搶玩具,如果同學不給他或沒有搶到,他就會打這個小朋友。媽媽要求他做什么事情時,如果他不想做了也會打身邊的小朋友。小付每次打完同學之后,媽媽都會罵他、用手打他,甚至有一次,媽媽把自己穿在腳上的高跟鞋脫下來,用尖尖的鞋跟往他腦袋上咣咣地敲。
面對小付出現的問題行為,我先指導媽媽給小付做行為 ABC 記錄。行為 ABC 記錄是“問題行為干預”中直接收集數據的一種方法。A(Antecedent)前事:就是行為發生之前有什么事情發生?孩子是否有身體上的不適?是否由于認知的局限導致行為的發生等等。B(Behavior)行為:就是行為的表現、嚴重程度、持續時間等。C(Consequence)結果:就是行為發生之后得到的結果是什么?也就是孩子得到什么?逃避什么?周圍人們的反應是什么等等。
下方的表格可以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行為ABC記錄:
A(前事)
B(行為)
C(結果)
老師輔助明明與另一個孩子共同玩一個玩具
明明打那個孩子
老師將明明領到一邊,讓他自己玩這個玩具了
老師要求明明做卡片分類
明明打老師
老師就不要求他做了,把卡片收起來了
老師給另一個孩子上課,明明自己玩
明明發脾氣,頭撞墻,用手拍自己的頭
老師制止他,然后抱他并安慰
然后,我根據記錄的數據與媽媽一起分析小付行為的功能,指導媽媽如何根據他行為的不同功能做出正確的干預。我明確地告訴媽媽不能用罵他、打他等以暴制暴的方式來應對和處理小付打人的行為,重要的是要防患于未然 — 提前預防和制止。
小付媽媽在我和其他老師的指導下積極應對小付的各種挑戰性行為,就這樣,小付還是天天狀況百出。
他不喜歡“星星雨”食堂的飯菜,等媽媽打飯回來,母子倆坐在餐桌跟前準備吃飯的時候,他當著媽媽的面把餐盤反扣過來將飯菜全部倒在餐桌上,然后跟媽媽說“走,去下館子”。飯菜被倒掉了,沒轍,媽媽只能帶他去下館子。
僅僅到了第二周,“星星雨”上到 60 多歲的保潔奶奶,下到3歲的小同學,從身高一米九幾、體重二百多斤的壯漢到弱不禁風的美女阿姨,沒有一個人能夠幸免于難,所有人都被小付打過、罵過。剛開始,小付媽媽還及時地給被打的人和被罵的人道歉,每天都不知道要給人道歉多少次,慢慢地媽媽也變得麻木了。
小付媽媽忘了給被小付打的人道歉,很快惹得一部分家長不高興了。
第三周剛開始,“星星雨”的領導收到一封有大部分家長簽名的聯名信,信上描述了大家如何受小付之害,苦不堪言,小付媽媽又不管她兒子等等。信中要求“星星雨”開除小付,如果不開除小付的話,這些家長就要退學回家,讓“星星雨”只教小付一個人!
當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的心情非常糟糕。
我沒想到的是,同樣是孤獨癥孩子的家長,卻不能接納另一個孤獨癥的孩子。
▲ Photo by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
收到這封信之后,“星星雨”的領導、教師和小付媽媽積極與其他家長溝通,說明了在面對小付打人的行為問題上媽媽和老師們所做的努力。經過坦誠的溝通之后,大部分家長表示理解并愿意和小付一家一起繼續在“星星雨”學習,但還是有少數家長堅持要求小付一家退學回家。
根據前兩周通過行為 ABC 記錄采集到的小付打人的行為數據的統計,我們發現小付和媽媽在一起時打人的行為出現得最多,數據說明了媽媽是誘發小付打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媽媽在短時間之內又不能像老師們一樣專業地應對,通過有效的干預來減少/消除小付打人的行為。綜合所有的信息,“星星雨”的教學團隊商議出一個折中的方案,從第四周開始,小付媽媽回家,把小付留在“星星雨”繼續接受個別化教育。小付白天在“星星雨”上課,放學后由老師帶回家,晚上和周末在老師家吃住,五位老師輪流帶小付,每人帶一個星期。經過商議,小付的爸爸媽媽和其他家長都接受了這個方案。
從第四周開始實施這個方案之后,小付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打人的頻率直線下降,其它的能力也得到了明顯的提升。
由于我們夫妻倆都是“星星雨”的老師,所以小付在我們家一住就是半個月。他第四周、第五周在我們家住的時候表現得還是比較拘謹,但他也會主動要求我們給他做什么好吃的飯菜,給他買什么樣的零食,周末帶他去哪里玩等。
第九周,小付第二次住進了我家。他這時已經和我們非常熟稔了,除了午餐在食堂吃飯不能點菜之外,他每天會提前跟我點好下一餐要吃的飯菜。
星期三晚上,小付和我們夫妻倆一起吃晚飯。小付在吃飯的時候,時不時地盯著我的飯碗看。
“你小子在看什么?”
“吳老師,你快點造。”
“吃這么快干什么?”
“你快點造,造完了我給你盛飯。”
等我吃完一碗飯的時候,小付不等我起身,就拿著我的碗到廚房去給我盛飯了。等他端著一碗滿得冒尖的米飯從廚房出來的時候,我都看傻眼了,我只能弱弱地問他一句“你盛這么滿干什么?”。
小付滿臉壞笑地看著我說:“造吧!造完了我還去給你盛”。
看到這個調皮小子也有這么可愛的一面,我就笑著對他說:“造不動了,這么一大碗都多了”。
小付看我沒有跟他生氣,就小聲地跟我說,“吳爸爸,明天早餐我要吃皮蛋瘦肉粥”。
我聽后一愣,不太確定地問了一句,“你剛才說什么?”
“明天早餐我要吃皮蛋瘦肉粥”。
“不是,我想問的是,你剛才叫我什么?”
“吳爸爸”
“你為什么叫我吳爸爸呀?”
“你就像我爸一樣!”
我一把抱住了小付,激動地對他說:“好的,明早我給你做皮蛋瘦肉粥”。
在這之前,我也教過一些能力比小付還要好的學生。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學生會叫我吳爸爸。小付成為了第一個管我叫“吳爸爸”的學生。那時,我雖然已經結婚了,但還沒有生孩子。
再次成為我的學生
隨著社會對孤獨癥群體認識程度的提高,醫院識別診斷能力的提升,中國內地被識別診斷的孤獨癥兒童的數量在不斷地增加,教育需求也在同步增加。但是,公立教育系統沒有起到應有的保障作用,因此更多的民辦特殊教育機構應運而生。
從 2002 年開始,全國各地陸續開辦了越來越多的民辦特殊教育機構。在 12 歲以上的青少年孤獨癥,只有 1% 左右障礙程度最輕的、能力最好的依然能留在公立教育系統內接受教育,剩下 99% 的 12 歲以上的青少年孤獨癥無處可去,只能留在家中/被鎖在屋里由家人照顧。
在此社會背景之下,2006 年 11 月 13 日,我帶領小團隊成立了中國內地第一個專門為 12-18 歲孤獨癥人士提供教育和養護的服務項目。
▲ 在這棟小樓內,誕生了中國內地第一個專門為12-18歲孤獨癥人士提供個別化教育和養護的服務項目,成立之初命名為:“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養護訓練部”。
青少部開學的當天,我又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 — 小付。
大家可能會奇怪,小付不是回家了嗎?他怎么又回到“星星雨”了?
2000 年 9 月 1 日,小付順利地進入當地的一所普通小學,成為了一名超齡小學生。
二年級第一學期,小付表現的還算好,能按照學校的要求準時上學、放學,但課業方面學習起來就比較吃力了。后來,老師上課講什么、教什么他都不聽不做了,但他還是能堅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聽不懂、不會做、還要在座位上干坐著,這是多么索然無味的一件事情啊?這時候他不僅需要課業方面的支持,還需要有人給予心理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夠根據他的狀況調整教育計劃,甚至做出不同的教育安置。對于小付面臨的挑戰,學校、社會、家人給予的有效支持幾乎為零。
二年級第二學期開學之前,媽媽在給小付準備學習用品。
小付對媽媽說:“媽,我不想去上學了。”
“你為什么不想去上學?”
“上學沒意思,他們都不跟我玩,還說我是傻大個。”
“你不去上學干什么?難道天天在家呆著嗎?不想去也得去。”
小付滿臉的沮喪,但又不敢繼續跟媽媽爭辯。
開學第一天,等小付吃完早飯,媽媽讓他背上書包去上學,小付極不情愿地跟著媽媽去了學校。媽媽把小付送進教室之后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順路買了中午和晚上的菜。
媽媽回到家門口的時候,小付已經背著書包在門口等著了(他沒有家門的鑰匙)。媽媽趕緊開門把菜放回家里,小付跟著進了門。媽媽放好菜,要再次送小付去學校。
小付開始大聲地叫嚷:“我不去上學,我不想去學校。”
媽媽好說歹說也沒用,拉也拉不動他。氣得媽媽順手抄起掃把就往他身上打,小付趕緊跑開。頓時,家里雞飛狗跳……
最后的結果就是,媽媽把小付揍了一頓,小付在家呆了一天。
第二天,媽媽把小付送進教室。媽媽回到家的時候,小付已經背著書包站在家門口等媽媽開門了。
這樣堅持了兩個星期,天天如此。
第三個星期,媽媽就不送小付去上學了。從此,小付再也不去上學了,在家過起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日子,稍不如意就摔東西、打人。慢慢地,小付成了爸爸和媽媽兩個家族中的二號人物。為什么說他成了二號人物呢?因為兩個家族中只有三舅才能管得了他,其他人都得順著他,稍不如意就會大發雷霆。
2006 年,小付的爸爸媽媽聽到了“星星雨“要開辦青少部的消息,第一時間給 16 歲的小付報了名。青少部開學的時候,小付再一次成為了我的學生。
無處托付的成年孤獨癥
“吳老師嗎?”一個略帶沙啞,從聲音中就能聽出情緒低落的女聲從我的手機中傳出。
“我是!請問你是?”
“我是飛飛媽媽。”
“噢!您換手機號了!飛飛現在怎樣啊?他挺好的吧?!”
“他,他……”之后傳來的就是這位母親的啜泣。
“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他,他的右眼瞎了……”
“啊!怎么回事?”
“他年滿 18 周歲從‘星星雨’青少部畢業后,在家呆了一段時間,我和他爸爸輪流請假在家照顧他。但是,我們也不能老請假啊!后來,我們千尋萬找,終于在外地(北京之外)找到了一家可以常年托養的機構。飛飛去了兩個多月了,我們也想孩子,我和他爸就開車去看望他。一見面就發現孩子的右眼不對勁,我們趕緊帶他回北京的專科醫院就診,醫生檢查后診斷為陳舊性視網膜脫落,視網膜脫落的時間最少一個月。”
“還能治好嗎?”
“醫生說時間太長了,無法治療了,只能是瞎了。吳老師,你說,他是孤獨癥已經夠可憐了,現在又瞎了一只眼睛,將來怎么辦呀?!你們怎么不收成年的孤獨癥人啊?”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結束的這次通話!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記得與飛飛媽媽結束通話后,我整個人癱在沙發上,不想說話,不想做任何的事情。
飛飛只是我教過的眾多學生當中的一個,他也是中國千萬孤獨癥人當中的一個。孤獨癥人也會長大,他們長大之后怎么辦呢?!
我把飛飛的境遇告訴了“星星雨”的同事們,聽聞之后深深地刺痛了大家的內心。在“星星雨”制定新的戰略規劃時,經過全員的討論,大家一致同意 — 開始探索并提供成年孤獨癥人的社區生活支持服務。
2021 年 9 月 1 日,我帶領團隊成立了“星星雨”成年孤獨癥人士服務中心,為成年孤獨癥人士提供個別化的社區生活支持服務和就業支持,希望能解決家長的后顧之憂。
雖然我從業至今已經過去了 27 年,但是將來我依然會致力于成為孤獨癥人士的代言人,在孤獨癥人與社會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但我在工作中最難的是,經常會有一種挫敗感和無力感。我教過的學生中,有一部分學生經過三個月、半年、一年的個別化教學之后,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認為他們可以去上幼兒園、上小學了,就建議家長帶孩子回去上幼兒園/上小學。但是,這部分學生中有 90% 要么在報名環節就被拒收了,要么是在幼兒園或學校沒呆幾天就被勸退了。當我聽到這樣的消息的時候,我經常在想,是不是我或者是我們(星星雨)做得不夠好,才導致他們被拒收或者被勸退了呢?
法國精神分析專家吉布爾先生告訴我,在法國,一般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因為接受教育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再者,為每一位公民提供教育,特別是為殘障人士提供合適的教育與支持性服務,需要動員整個社會的資源才能做到。
▲ 2014 年 3 月,Michel Guibal 先生第十五次到“星星雨”做專業志愿者,為中國的孤獨癥人家庭做心理咨詢。左:Michel Guibal,右:吳良生
的確,我的陪伴與支持只是每一個學生人生長河中的一個階段而已,我無法陪伴/改變他的一生,只要盡了最大的努力,作為老師的我就問心無愧了。
(文章投稿自曉更基金會與雨滴傳播主辦的心智障礙議題生命故事寫作營項目。奴隸社會授權轉載)
2008年,壹基金發起典范工程項目,星星雨是該項目的首批首家入選機構。頒獎現場,李連杰先生表達會用自己的力量幫助星星雨、讓更多人支持孤獨癥人士。2010年,在李連杰先生的支持下,星星雨志愿者、導演薛曉路女士以星星雨的故事為原型,拍攝了中國首部孤獨癥題材電影《海洋天堂》,讓更多公眾開始認識孤獨癥。
2011年,壹基金正式發起海洋天堂計劃,以孤獨癥、腦癱、罕見病等特殊需要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以社會倡導為主要策略,通過搭建與支持特殊兒童服務機構、家長及病友組織、研究機構、公眾和企業的聯合行動網絡,有效促進社會接納及政策支持,幫助特殊需要兒童及其家庭享有有尊嚴、無障礙、有品質的社會生活。
其中,壹基金與星星雨已連續合作15年,作為海洋天堂計劃華北網絡(心盟網絡)的樞紐機構,一起聚焦議題,開展網絡建設、聯合勸募、聯合行動、聯合倡導等行動。
壹基金以“盡我所能、人人公益”為愿景,專注于災害救助、兒童關懷與發展、公益支持與創新三大領域,是5A級社會組織,連續十一年保持信息公開透明度滿分。感謝壹家人支持,歡迎壹家人監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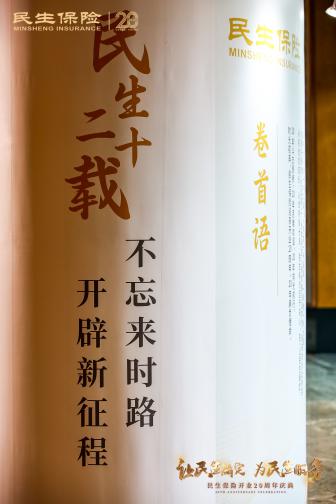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